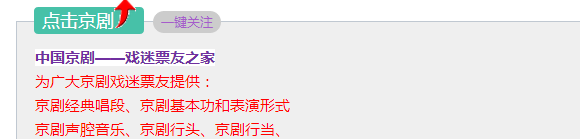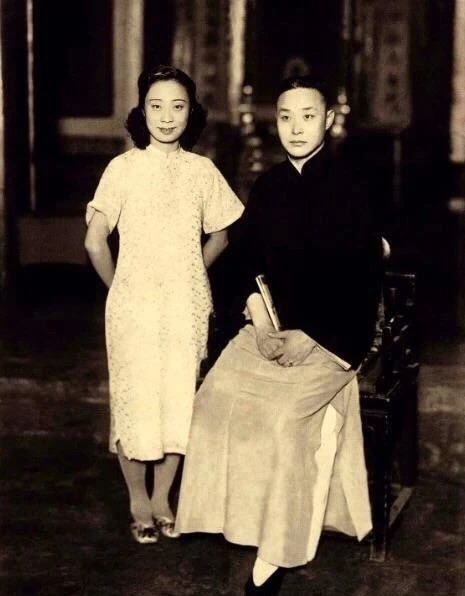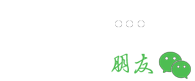津然
管理员
21-7-10
浏览317
发表于上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