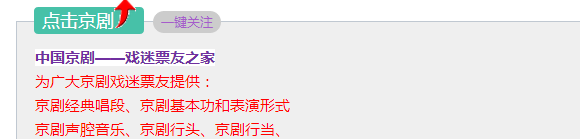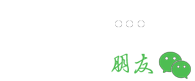【京剧人物】栗培敏:怀念我的老师沈雁西先生
文/栗培敏
图一:
1981年沈雁西与栗培敏师徒合影
又是一年清明。2016年的清明是敬爱的沈雁西先生逝世35周年的日子。35年前的4月23日,沈老师离开了我们,离开了他热爱的京剧舞台。时光穿梭,往事历历。我跟随着他从艺的寒暑春秋、到过的京、津、苏、浙、皖各地,一幕幕当时的情景浮现在眼前。仿佛,我又看见他梳理好一丝不乱的头发,足蹬一尘不染的皮鞋,叫上我一块儿上剧场演出去……
初遇沈雁西先生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们这些刚从上海戏校毕业的学生,和京剧院学馆毕业的学员组成了一个演出团体,被下放到上海东南海滨奉贤的“五七”干校劳动。当然,抓革命还得促生产。从清晨出工回来到午饭前的时间,是我们练功调嗓的时候。在宿舍的尽头,有一间草顶、泥墙、无门的大草料棚。那天我和学馆的一位唱旦角的叫乌江的同事,从宿舍搬了个凳子,拿了把胡琴到那里调嗓子。《红灯记》铁梅的唱段“听罢奶奶说红灯”一曲刚落,草棚里出现了一位中年男子。看来他在外面听了一会了。“沈老师!”只见乌江称呼他道。她给我介绍说:“这是京剧院的琴师沈老师!”并向沈老师介绍,我是戏校毕业的,在学校跟倪秋平老师学习。沈老师笑嘻嘻地夸我手音不错。听到别人夸奖,心中自然开心。随即我让过那张唯一的凳子,并把胡琴递上去,请沈老师拉一段。只见他刚才还是满脸的暖暖笑意,即刻变得苦涩起来。“不行,不行。我不能拉,不能拉的!”说完后他即刻转身匆匆地离去,一脸茫然的我看着他渐渐消失在了农田的尽头,后来我才知道,沈老师在京剧院被打成“里通外国的反动学术权威”,是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“牛鬼蛇神”,没有得到工、军宣队的允许,他是不操琴的。那时同样遭遇的还有名须生言少朋老师(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),他也不能唱。但他拉得一手好胡琴,每天劳动结束后,给“革命小将”调嗓子,有求必应。
师从沈雁西先生
图二:
栗培敏与沈雁西夫妇合影
冬去春来,此后我就没有再见到沈老师,直到“文革”结束以后。1977年,我们演出团体的人员都分到了由“样板团”为主组建成的上海京剧院。我分到了以《智取威虎山》样板团为主体的上海京剧院一团。其中有纪玉良、张学津、王梦云、夏慧华等名角。
“文革”结束,百废待兴,精彩纷呈的传统戏重现于舞台。夏慧华要演梅派名剧《宇宙锋》,请来了二团的梅派琴师为她拉京胡。乐队的其他下手都是我们一团的,我拉京二胡。在排练厅里,我又见到了当年干校中黯然离去的沈雁西老师。《宇宙锋》就是我和沈老师合作的第一出戏。记得当时,那一段【反二黄】“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”拉下来后,沈老师放下胡琴,为我鼓掌。我知道,这掌声并不意味着我拉得多么出色,这里面蕴含了很多含义:鼓励,感慨,欣慰……
恢复传统戏后,沈老师成了大忙人。一团的夏慧华唱戏要请他,而他是二团的人,李炳淑演出也非他莫属。那时,他往往是天蟾拉完夏慧华上半场,赶包到大舞台接李炳淑的下半场。她俩都各有自己的粉丝,聚拢在剧场门口或休息厅,评头论足。等琴师来了,这才进场看戏。过了不久,文艺界兴起了一股拜师收徒的热潮。由京剧院出面,演员、乐队、舞美,各有师徒在职工食堂举行拜师仪式。乐队方面,沈雁西老师和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师徒,我开始正式跟随沈老师一起工作,做他的副手,拉京二胡。回想起干校一幕,这也是一种缘份吧。
沈老师是一位通达、慈祥、负责任的好老师。他不是生搬硬套地说教,而是把他操琴的经验和要点告诉我,用他对唱腔的感受启发我,没有一点老戏班师父的架子。有时候,甚至我会把自己对操琴的理解和建议告诉他,他觉得合理的,会立即采纳。他教新段子,会先叫我唱会。记得他给过我一盘带子,是他哼唱的《太真外传》中杨玉环祝告双星时唱的“四愿”歌,叫我学唱。可惜那时由于卡式磁带很少,后来我在录其他东西时把它覆盖掉了,现在想来真是追悔莫及!
图三:
1981年沈雁西、栗培敏为夏慧华操琴
图四:
1981年沈雁西、栗培敏为李炳淑操琴
沈老师是一位开明而不保守的老师。1980年,张君秋先生率团到上海演出,沈老师把我介绍给了张似云老师。他总是希望我博采众长,多吸收些东西。一天早上,他把我带到北京团住宿的沪江饭店,让我拉给张老师听,请他指点。晚上我又到剧场,坐在下场门乐队的侧幕旁观摩。第二天,沈老师请张老师去思南路家中做客。饭前,他们合作了梅派戏《天女散花》。曲罢,老师赞叹地对我说:“张老师现在虽是拉张派的高手,可是拉起梅派来不夹带张派,还是正宗的梅派!”虽然,这只是那时的一句赞美之词,但是我的记忆尤为深刻,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,努力去做到沈老师所赞扬的那种境界。京剧的流派不仅是唱腔和唱法上的风格各异,操琴的不同手法所形成的不同风格也是各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右手执弓,推拉的长短,顿挫、缓急、轻重,左手摁弦,揉、打、滑、抹等各种处理,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这些技术上的手段,再加上琴师自身对各流派的感悟,成就了有血有肉的音符。反之,就成了我们业内所说的“官中”胡琴(指会的很多却没有风格特点的琴师)。
沈老师除了指导我配合拉京二胡外,还竭力培养我拉京胡。可我自己觉得还不成熟,不敢拉。沈老师却说“怕什么,我帮你拉二胡,保着你。”这让我感动不已!有这么好的老师护航,我还怕什么?通过努力,我在舞台上成功地为夏慧华伴奏了《断桥》、《凤还巢》两出戏,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。
沈老师不仅是一位善良真诚的老师,还是一位时尚的老师。闲暇时,他会教我们吃西餐的规矩和常识,皮鞋怎样保养,怎样给皮鞋上油会又省力又光亮,衣服的颜色该怎么搭配等等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,他告诉我们咖啡色和黒色是不能搭在一起的。有一天,沈老师拿着一张纸条递给我说:“栗培敏呀,起个英文名字吧。我帮你想了几个,写在纸条上,你挑一个。”沈老师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学生,英文很好的,那时改革开放不久,学习英文是件时髦的事。我在他选的名字中挑了一个与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齐名,又和上海话“来赛”(真行的意思)有些谐音的名字,从此我就有了一个英文名——Nancy(南希)。
告别沈雁西先生
1981年夏季,李炳淑受安徽方面邀请,以小组的形式到芜湖去演出。那时李炳淑因为前有样板戏《龙江颂》,后有电影《白蛇传》的影响,人气很旺。再加上她又是安徽人,因此在芜湖的演出盛况空前。那个年代,在闹市街头,经常能看见一些追求时髦的人,手提大大的录音机,放着音量超响的流行音乐。可是我们在芜湖和平大剧院演出的那几个夜晚,每当散戏后,剧院前的大街上到处是兴趣盎然的观众,他们也手提大大的录音机,开着超大的音量,放的是我们刚演完的《玉堂春》。我们跟在散场的观众后面回饭店,那种景象真是棒极了。因为在芜湖演出很成功,我们又被邀请到安庆去演出。那时沈雁西老师有一台质量很好的小录音机,是他的海外亲戚送的。每天晚上演出,他都会录音。散戏后,回到酒店,乐队的人围坐在一起,一面吃着夜宵,一面欣赏自己的作品。一番评说,几许赞赏,其乐融融。踌躇满志的沈老师,倾心地品味着他的京剧,尽情地享受着他的人生。
图五:
沈雁西(左二)在上海京剧院收徒仪式上发言,左一为郭坤泉,右一为沈金波,右二为孙正阳
安徽之行也许是太辛苦了,加上遇上老友、学生,喝了些酒,老师的痔疮病有点复发了。
回沪后,唱片公司邀李炳淑去录音,准备出版一套她的唱腔集。10月19日、20日、21日,3天的录音时间里,沈老师显得有些疲惫。不知怎么的,琴放在右腿上会有疼痛感。我问他是肌肉疼还是骨头疼,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每当录音中途休息时,一向很注重仪表的沈老师会躺在休息厅的地毯上休息。当时我们都劝沈老师去好好检查一下,休整一段时间。
一周后,从师娘口中得知, 沈老师得了绝症,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。那年年底,梅葆玖先生和童芷苓女士应邀赴香港演出,梅先生本想邀请沈老师同去合作几出戏。当时赴港人员都集中在上海京剧院排戏。可是等梅先生到思南路家中去邀请沈老师时,沈老师已卧病在床,不能如愿。事后,沈老师还安慰我说:“这次不成,等我身体好了,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”(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况)后来,我虽有同梅葆玖先生同台的机会,可已不是为沈老师拉京二胡了。
那时的沈老师还希望在康复后,把自己几十年的操琴经验和体会写成文字,为求图文并茂,还想让我拿一个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他执琴、推弓的姿势及手法。可惜终未如愿。
1981年的冬天,是沈老师与病魔抗争的冬天。那年冬天,沈老师床前的水仙花开得特别茂盛,我们都期望能有奇迹出现。
但当春暖花开、大地复苏之时,敬爱的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也是在那时,唱片厂录制的梅派唱段第一集出版了,我们录了那么多段子,出版方编辑发行的那盘带子竟是《生死恨》、《太真外传》。悲凉、飘渺的旋律伴随着尊敬的沈雁西老师离却了凡尘……
弃商从艺为梅兰,荏苒岁月丝竹伴。
正当展翅任飞时,天庭传唤列仙班。
金声余音不觉远,德艺薪火有人传。
若闻苍穹传天籁,应是沈公调音弦。
本文由栗培敏老师提供,谨致谢意!
转自 青衣童儿京剧道场